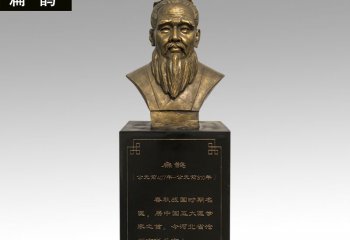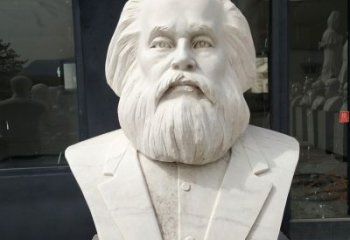摘要∶北島∶“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shuō)我還有什么夢(mèng)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zhì)主義昏夢(mèng)中醒過(guò)來(lái),通過(guò)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fēng)貌和精神品質(zhì)。大幕正在拉開(kāi),舞臺(tái)徐徐轉(zhuǎn)動(dòng),那些為民族文化復(fù)興做夢(mèng)的人開(kāi)始行動(dòng)。

”來(lái)源于∶《南都周刊》羅小敷詩(shī)人北島說(shuō),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國(guó)家,現(xiàn)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北島告訴我:“那些批評(píng)我的人存在黨同伐異的一面,網(wǎng)上很多化名謾罵的人沒(méi)有讀懂我的意思,我認(rèn)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復(fù)興,民族的命脈還是要靠文化和文字傳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島仍是無(wú)法擺脫某種家國(guó)情懷。

近幾年來(lái),詩(shī)人北島連續(xù)入選各種版本的“華人公共知識(shí)分子”名單,現(xiàn)在看起來(lái),他的生活與內(nèi)心,仿佛已寧?kù)o下來(lái)。但是他不這樣認(rèn)為。他說(shuō),我現(xiàn)在是老憤青一個(g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rèn)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門(mén)開(kāi)》這本書(shū),“在我的城市里,時(shí)間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線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廟恢復(fù)原貌…

我打開(kāi)城門(mén),歡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歡迎無(wú)家可歸的孤魂。”在新書(shū)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門(mén)內(nèi)的主人。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沒(méi)有停止尋找。寫(xiě)于1994年的詩(shī)作《背景》中,他說(shuō),“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返故鄉(xiāng)”,其實(shí)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絕望感。

后來(lái)又有詩(shī)作《回家》,詩(shī)中他放任夢(mèng)境中的感性,飽含濃濃思鄉(xiāng)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寫(xiě)下《黑色地圖》,家已經(jīng)變了,回鄉(xiāng)治好了思鄉(xiāng)病。2008年,北島接受香港中文大學(xué)的邀請(qǐng),定居香港。從歐洲到美國(guó),再到香港,漂泊已經(jīng)是一種生活方式,北島說(shuō)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來(lái)最安定的,離北京也最近。而對(duì)于故土,他說(shuō)除了牽掛住在北京的90歲老母親和親朋好友外,對(duì)現(xiàn)在的北京毫無(wú)依戀,“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經(jīng)沒(méi)什么關(guān)系。

”對(duì)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歲的人倔強(qiáng)地否認(rèn)著落葉歸根的情結(jié)。而在書(shū)房樓下的粵菜餐廳,我們閑聊的話題從頭至尾卻幾未離開(kāi)過(guò)故土。在每一次話題即將陷入沉默時(shí),他問(wèn)起內(nèi)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狀況,問(wèn)起房?jī)r(jià)物價(jià),甚至對(duì)年輕人談戀愛(ài)的方式也很好奇,他們還會(huì)不會(huì)相親?北島曾答應(yīng)將自己一篇關(guān)于攝影的訪談給韓寒辦的雜志《獨(dú)唱團(tuán)》用,沒(méi)想到卻遭到幾個(gè)文人朋友的反對(duì),他又好奇地打聽(tīng)韓寒到底是個(gè)怎樣的年輕人,“我開(kāi)始關(guān)注他的言論,他在變,變得成熟了,但最終到底能走多遠(yuǎn),還不好說(shuō)。
”去年,北島在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對(duì)未來(lái)發(fā)出的9封信—致2049的讀者》,他寫(xiě)道:“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shuō)我還有什么夢(mèng)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zhì)主義昏夢(mèng)中醒過(guò)來(lái),通過(guò)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fēng)貌和精神品質(zhì)。”在文章的最后,北島說(shuō):“大幕正在拉開(kāi),舞臺(tái)徐徐轉(zhuǎn)動(dòng),那些為民族文化復(fù)興做夢(mèng)的人開(kāi)始行動(dòng)。”但文章引起了一些爭(zhēng)議,批評(píng)者認(rèn)為北島如今變得功利了,向歲月投降了。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學(xué)舉辦的香港城市文學(xué)節(jié)上,北島與一眾港臺(tái)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臺(tái)上。港臺(tái)文化人多具備談笑風(fēng)生的口才,臺(tái)下聽(tīng)眾陣陣笑聲。北島穿著淺灰色西裝,緊鎖眉頭端坐其中,他發(fā)言的主題是《詩(shī)意地棲居在香港》,規(guī)勸香港年輕人通過(guò)詩(shī)歌,在高壓的現(xiàn)世中尋找精神家園。北島:2001年底第一次回鄉(xiāng)之旅感情很復(fù)雜,這首詩(shī)題目就自相矛盾,地圖是確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種屏蔽。
回鄉(xiāng)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個(gè)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這行當(dāng)?shù)暮锰幨牵梢杂梦淖种亟覉@,重建一個(gè)業(yè)已消失的世界。北島:漂泊那些年,我會(huì)想起胡同,北京的氣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鄉(xiāng)治好了我的思鄉(xiāng)病了。
后來(lái)也回去了幾次,但現(xiàn)在對(duì)北京沒(méi)有可依戀了。不一樣要?dú)w根了,天涯何處無(wú)芳草。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國(guó)家,現(xiàn)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這種漂流穩(wěn)定多了。漂流已經(jīng)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沒(méi)有認(rèn)為一定要回到那個(gè)地理上的家。現(xiàn)在的北京像一個(gè)現(xiàn)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標(biāo)本,和我的童年記憶完全隔絕了。北島:張棗最近去世對(duì)我打擊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們都是無(wú)話不談,他也曾是《今天》雜志編輯,回國(guó)后就是被環(huán)境毀掉的例子。
這跟他的個(gè)性有關(guān),太容易受環(huán)境影響,生活狀態(tài),詩(shī)歌創(chuàng)作都被毀壞了。大陸的知識(shí)分子被學(xué)院化、體制化比較嚴(yán)重,獨(dú)立批評(píng)的聲音越來(lái)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點(diǎn),不知道我回去會(huì)不會(huì)有同樣的問(wèn)題,現(xiàn)在保持一定距離,有清醒的狀態(tài)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間,沒(méi)什么限制和顧慮。
我想在余生好好寫(xiě)東西,做一點(diǎn)事。繼續(xù)辦雜志,組織香港詩(shī)歌節(jié),做文化活動(dòng),對(duì)漢語(yǔ)文化圈有一些幫助。北島:70年代,大家在地下掙扎;80年代大家都在發(fā)揮能量。90年代出現(xiàn)分化,有個(gè)人的,也有歷史轉(zhuǎn)折,有權(quán)力和資本的關(guān)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壞的十年,知識(shí)分子在體制化之后獨(dú)立聲音都沒(méi)了,缺乏開(kāi)放的、可以真正討論問(wèn)題的氣氛。北島:我認(rèn)為這是這些年普遍的現(xiàn)象,近十年,體制化、學(xué)院化讓很多人變成專家,不再對(duì)社會(huì)和中國(guó)文化有獨(dú)立的聲音。黨同伐異的現(xiàn)象很嚴(yán)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間欲置對(duì)方于死地的立場(chǎng)化現(xiàn)象嚴(yán)重。
北島: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棄對(duì)世界大問(wèn)題、真問(wèn)題的關(guān)注,變成了私人恩怨。知識(shí)分子大談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對(duì)這種整體的趨勢(shì)感到很失望。北島:香港是一個(gè)過(guò)路碼頭,來(lái)往的人很多,可以見(jiàn)到各種想見(jiàn)的朋友。網(wǎng)絡(luò)也讓信息來(lái)源不成為問(wèn)題。
北島:我接觸的人很雜,學(xué)者型的知識(shí)分子接觸不多,有時(shí)我怕太學(xué)術(shù)化的文人。我自己沒(méi)什么知識(shí),對(duì)學(xué)術(shù)不敢興趣,讀的很有限。北島:我現(xiàn)在依然很憤怒,老憤青。憤怒不一定要語(yǔ)言表達(dá),憤怒不是罵人,需要保持一種克制,情緒的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間需要張力。寫(xiě)《城門(mén)開(kāi)》時(shí)很憤怒,反而文字是收斂的。北島:作家通過(guò)寫(xiě)作發(fā)聲,一個(gè)作家應(yīng)該永遠(yuǎn)要跟他所在的時(shí)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語(yǔ)言保持緊張的關(guān)系。
如果沒(méi)有,就別做作家了。現(xiàn)在中國(guó)大部分人缺少這種緊張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