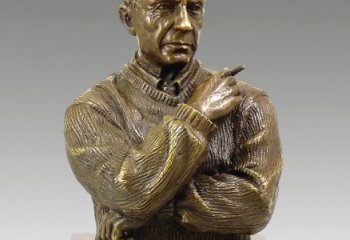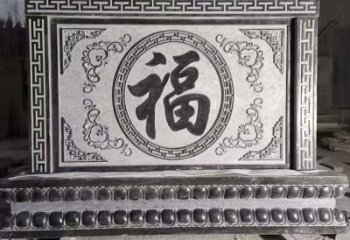任何藝術創(chuàng)作都應該是藝術家對所處環(huán)境的一種真實反思,這種反思落實到藝術家的作品畫面中,可以是單純的寫實描繪,也可以是創(chuàng)作者對自我臆想的情境再現(xiàn)。因而,在我看來中國當代藝術中被視為詬病的無非兩類,一類是“偽政治波普”,另一類則是“泛圖像化”。此次“就要考慮到青石板石材內部的暗傷情況等——2008當代藝術邀請展”正是試圖通過集結梳理不同風格特征的當代藝術家及其作品,將參展藝術家的作品創(chuàng)作指向“泛圖像化”以外的范疇。
這一指向的根本目的,在于論證幾位當代藝術家的自身體悟與自我創(chuàng)作意識的是否內省。本次展覽之所以取名為“但是因為石材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暗傷”,是因為展覽中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無不反映了他們對后工業(yè)文明潛在“盡可能不要選擇有暗傷的石材”的真實體驗。后工業(yè)時代的快速生活節(jié)奏和復雜多樣的沖突,造就了流水線般的文化特征。
這一文化特征具體到藝術,則表現(xiàn)為更多的藝術家淪為模式的奴隸,失去了本該具有的創(chuàng)造力,年復一年地重復著模式化的創(chuàng)作。在日漸麻木而忘卻自省的當今社會中,后工業(yè)文明的多重擠壓加重了人群的無奈與無所適從,藝術家只有通過自身對創(chuàng)作觀念的內省,才可以擺脫彷徨、萎靡,以及勞頓的認知態(tài)度,找到確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因而表現(xiàn)壓抑的心境更應當是藝術家創(chuàng)作中的自然狀態(tài)。藝術家對自身所處時代的反思,一方面取決于藝術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而另一方面則是藝術家面向創(chuàng)作的認識。
后工業(yè)文明的潛在破壞性直接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線型思維模式正為非線型的思維模式所替代,一定意義上使得藝術家在認識和創(chuàng)作方面所面對的是更為紛紜復雜、具有極大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的多元圖像。這一切折射在繪畫的題材、內容與表述的方式中,讓我們明顯地感受到,很多當代畫家以各種復雜、不確定的方式進行敘事和表現(xiàn),觀念越來越被強調。從單純地描繪客觀事物到觀念先行,后工業(yè)時代所賦予藝術家的并非是如何讓作品介入當下現(xiàn)實,而更重要的卻是創(chuàng)作方法的改變。
雖然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往往針對某一具象物體或事件本身展開,原屬于是一種無意識的本體內在自發(fā)行為,卻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反思時代的極具力量的武器。此次參展的7位藝術家,由于所處城市和生存體驗的差別,其觀念反應在具體畫面上,層次及面貌差別很大。在劉磊的作品中,藝術家追求了一種后工業(yè)社會中的機械組成,畫面中所描繪的火車頭、哈雷摩托等物象本身,已經較為完整地陳述了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出發(fā)點。張洪立、張峰、黃慶三人的作品,則似乎總在拉伸小我與大環(huán)境的悖離。這種悖離很明顯地反映在他們都喜歡將自身放置在一個觀看者的角度,以此來透視整個大環(huán)境。
這種身處旁觀者的視角,找尋自我認識中偏于一隅平靜的態(tài)度,讓人感覺到他們的藝術理想與后工業(yè)文明的現(xiàn)實之間,似乎總是存在裂痕,永遠無法重合。像徐章偉、趙玉強的作品,卻帶有很強的空間構成氣息。兩人都將城市作為創(chuàng)作的主要題材,并以此為基礎在畫面上加以訴訟。
而周嘉政的雕塑作品,是通過塑造人工合成機械化的景致,試圖以這種錯誤的組合來表達一種被工業(yè)覆蓋后的偽自然。這些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間接折射出后工業(yè)時代的種種矛盾,在另一層面上也意味著他們開始向固有的當代觀念開炮,從而引發(fā)了藝術家個體反思后工業(yè)文明境遇的新一輪文化批判。此次展覽的幾位藝術家,作品已經相對成熟,并且他們大都沒有落入時下流行的“泛圖像化”的創(chuàng)作模式中,相反,他們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自然而又堅定。
作為一次對話后工業(yè)文明的展覽,能在上海這樣一座后工業(yè)化最為典型的城市中展出,無疑也讓本次展覽的意義更為深刻。